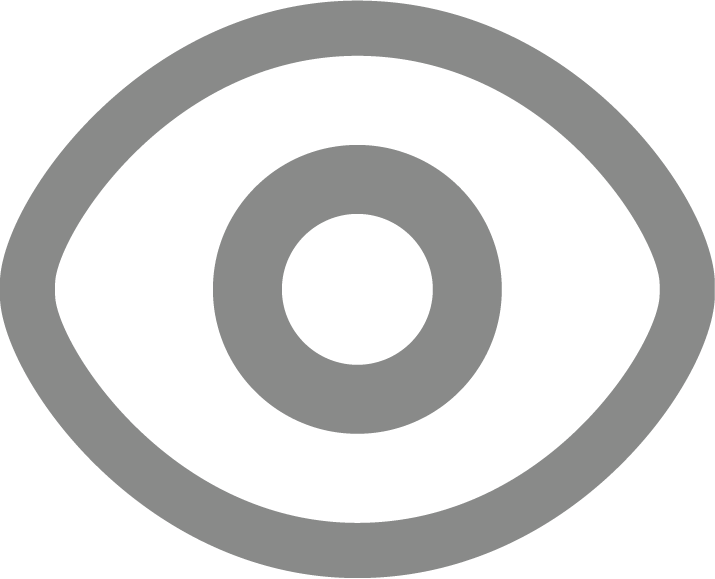DS关系的困境:自由与归属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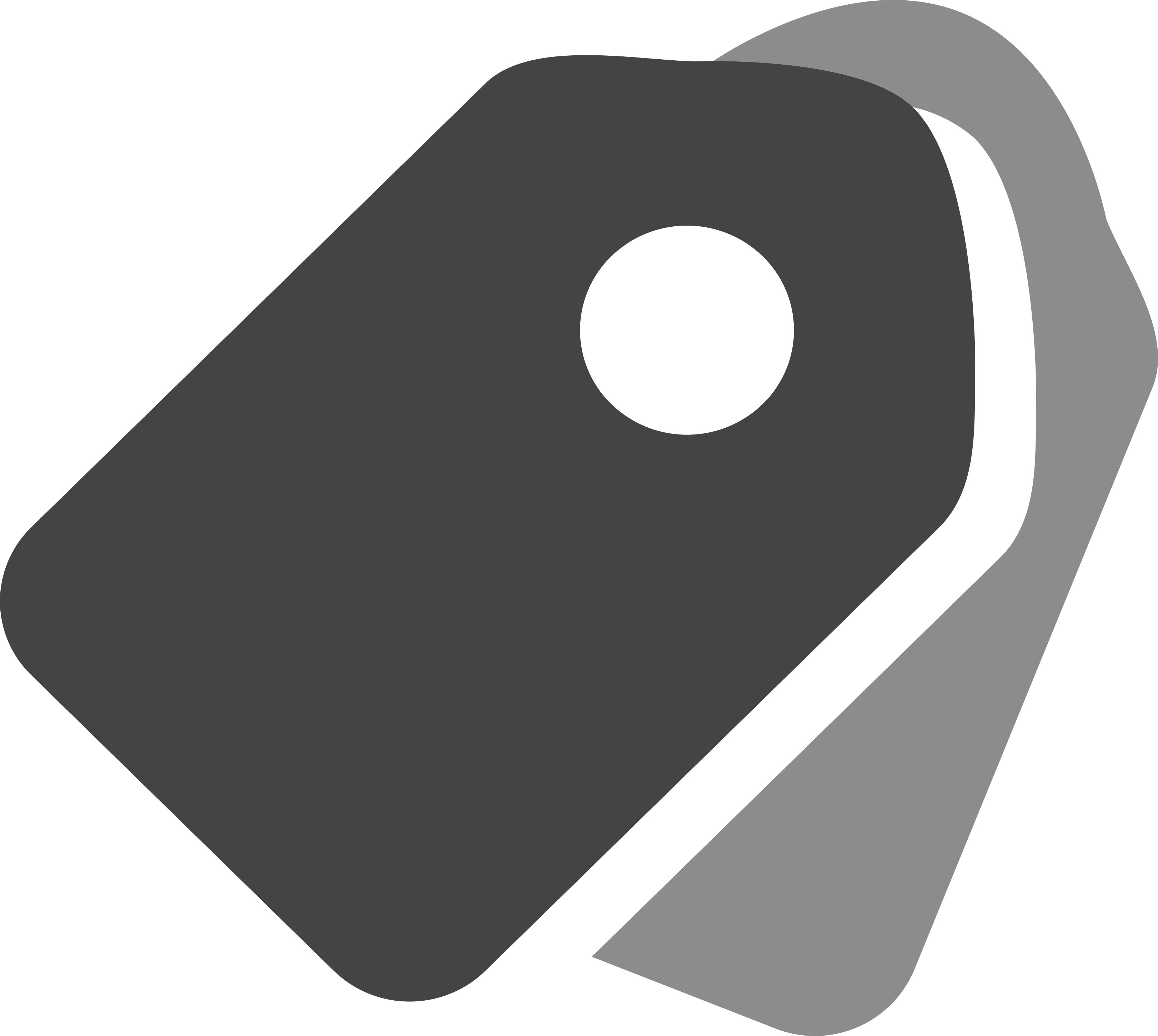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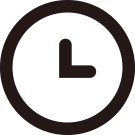 2025-02-14
2025-02-14最近我再度翻阅了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著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书中对现代人的刻画十分独特:现代人仿佛是充满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内心强烈渴望挣脱传统权威的桎梏,另一方面又被自由所带来的孤独与沉重的责任所深深困扰,最终无奈地选择将自我交付给新的“主宰”,这些“主宰”可能是极权主义的领袖,也可能是消费主义的洪流,亦或是某种精神层面的依赖。这种对于自由的逃避模式,与Dominant/submissive(DS)关系的核心逻辑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系:就像《神奇女侠》(Wonder Woman)的创作者马斯顿(William Moulton Marston)教授所提及的那样,当一个人主动且自愿地把控制权交给自己深爱的支配者时,这究竟是在重演“逃避自由”的悲剧,还是在开创一种更为深刻的自我解放的途径呢?
自由的矛盾境地:孤独的觉醒者
弗洛姆曾明确指出,人类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以及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原始纽带”之后,并没有如愿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反而陷入了个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困境之中:积极自由,意味着自我实现以及创造性潜能的充分发展;而消极自由,则呈现出一种孤立无援、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的生存状态。
现代人就如同被遗弃在荒原上的孤儿,不得不独自去应对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这种由不确定性引发的焦虑催生出了三种逃避的方式:权威主义,即放弃自我,依附于他人或者某种体系;破坏欲,通过毁灭来消除内心的无力感;机械趋同,让自己变成社会机器中一个标准化的零件。
DS关系中的权力转换:受控的“安全庇护所”
在DS关系里,服从者(submissive)通过契约的形式,将自己的决策权让渡给了支配者(Dominant),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弗洛姆所批判的“权威主义逃避”的再现——用服从去换取内心的安全感。举例来说:存在着规则与惩罚体系,服从者按照明确的指令行事,以此来逃避自由选择所带来的风险;身份被符号化,借助特定的称呼以及仪式性行为来构建权力等级,从而模糊自我的边界;在情感方面产生依赖,把支配者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以此缓解存在主义所带来的孤独感。这种关系动态与弗洛姆所描述的“受虐倾向”极为相似:通过自我贬低,将生命的意义寄托在他人的掌控之中。
DS关系的变革性:对“逃避自由”的全新解读
虚假的逃避与真实的觉醒弗洛姆的批判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上:逃避自由是一种无意识的、病态的妥协行为。然而,DS关系的关键在于双方清醒的知情同意:安全词(Safe Word)机制的存在,使得服从者拥有随时终止权力游戏的自由,这也证明了服从者从未真正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场景化权力,大多数的实践活动都限定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比如卧室或者约定的场景),不会对日常生活中的自主权造成侵蚀;它还是一种自我探索的工具,通过角色扮演,个体能够直面自己潜意识中的欲望与恐惧,从而实现弗洛姆所倡导的“积极自由”。从这个层面来讲,DS关系或许是一个对抗异化的试验田——通过模拟权力结构,参与者反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识别并拒绝现实生活中那些隐性的压迫。
支配者的矛盾之处:权力背后的责任与救赎弗洛姆认为,在权威主义中,“施虐者”往往通过控制他人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虚无感。但DS关系中的支配者角色却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伦理内涵:权力即服务,支配者必须将服从者的身心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其权威来源于服从者的主动赋予;镜像疗愈,很多支配者在掌控他人的过程中,反而能够治愈自身的不安全感(比如童年时期所遭受的创伤等);爱的技术化,在严格规则之下的亲密互动,成为了对抗现代人际关系疏离的有力武器。这种权力关系更接近弗洛姆所理想的“生产爱”的模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个体的成长。
超越二元对立:DS关系作为存在困境的一种解答
有限自由中的创造性DS关系所带来的真正启示在于:自由并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通过自愿地让渡部分自由,参与者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存在主义的微观模型:责任的重新分配,服从者将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焦虑(“我该做些什么?”)转移给支配者,从而获得更多的心理空间来专注于自我觉察;权力的美学化,指令和惩罚被转化为具有艺术性的仪式,痛苦与快感成为了存在真实性的感官证明。
共同体重建的理想蓝图弗洛姆期望通过“自发性的爱与劳动”来构建一个新的人道主义社会,而DS社群正在实践一种小型的共同体模式:契约伦理,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取代了模糊的社会契约,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猜忌;脆弱性的共享,支配者和服从者共同袒露自己情感上的弱点,打破了现代人之间的情感隔阂;反消费主义的抗争,通过身体的互动而非物质的占有来获得满足感。这种共同体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却为弗洛姆的哲学困境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感的答案。
人类对于自由的恐惧与渴望始终如影随形。当现代社会将个体推向价值虚无的深渊时,DS的实践者们选择以一种戏剧化的权力交换方式,在自我设定的“牢笼”中尝试“飞翔”——或许就像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并且不把任何外物当作终极目标时,他才能够真正拥有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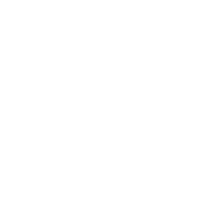


 142
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