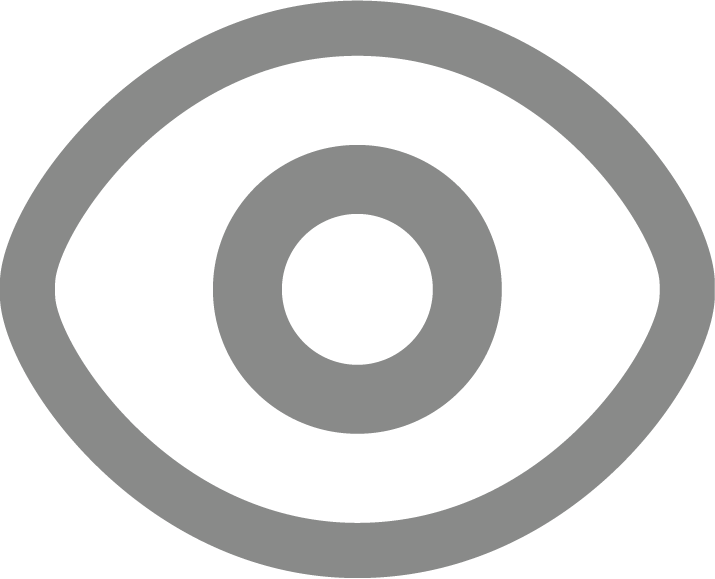我们都是抖M!关于《虐恋亚文化》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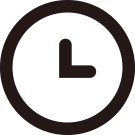 2022-03-14
2022-03-14想起本科时的一次专业课,主体是做一张海报,表达旺仔QQ糖的Q弹。想来想去,我就把旺旺的公仔P到了水晶球里,加了一个动感模糊的滤镜,营造出一飞冲天的效果,现在想起来觉得十分好笑。
想到此,依葫芦画瓢,根据字面为“抖M”做下“注解”,以祭奠我与日未曾的平面技术。“M”是个非常精彩的字母,放在此处十分得当,除了是其是英文单词的大写首字母,其“形态”也是十分具有象征意义。

抖M:“抖”是日语“ど(ド)”的音译,有“非常、超级”的意思。这里的“M”是指十九世纪的奥地利作家马索克(Masoch),而他的理论被成为Masochism,即受虐。
亚文化:即subculture,又称小文化、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与主文化相对应,是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比如服装街拍、同性恋等等,带有很强的后现代特征。
李银河老师在《女性主义》第一章中讲到到女性主义的四个派别,即自由女性主义、社会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以及产生最晚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不等同于女权主义,却又与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时常对于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产生理解上的困惑(希望日后可以谈及),从我们熟知的Georgia O'Keeffe笔下带有浓重生殖崇拜的的大花朵,Marina Abramović自虐式的激进行为艺术,到家喻户晓的弗里达·卡洛笔下未剪断脐带的婴儿再到Kiki Smith 流血的女人体(雕塑),这无不引起我强烈的求知欲。在艺术史上往往会有被我们忽略的细节,比如伟大的雕塑家罗丹有一个十分有才华的情人卡蜜儿,弗里达的伴侣是起初对于她十分赞赏的老师,女性伴侣的天赋异禀有时会使男性艺术家产生本能的惶恐,而反之(女性为主体)则往往不会。之于近期受到众多争议的央美研究生葛宇路将男性生殖器置于学校旗杆顶端的行为,我不禁想起央视雄起的大裤衩和上海陆家嘴事件,至于其是否带有一丝关于“主体与客体”的探索,我就不予以评说。
对于女性主义分支中的心理分析派来说,研究范围是上段中提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就是狭义的谁上谁下的问题。激进女性女性主义则把着眼点放到了之于女性之上的暴力、性、生育等问题。这两方面是复杂而交融的,其交集可以引出一个“小众”的话题即“虐恋”(sadomasochism)。这里的“小众”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在《虐恋亚文化》中李银河教授提到通过对样本分析得出的有待考量的“30%”(性行为中有虐恋倾向的比例),即事件发生的比例如果超过30%,那么它是否还能被冠以“小众”。下文中,我希望介绍这本书中我个人十分感兴趣的层面,包括社会受虐倾向。简单一提的是主标题的“抖M”其实是二次元文化范畴的词汇,不完全等同于此处的“Masochism”,所以,请原谅我的标题党行为。
此M和彼(通常意义)M
在书本的结构中,结尾处提及人类史上的两次性解放运动。我希望将此也就是虐恋的文化背景提于正文伊始。
有理论家提出西方第一次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于服装,也正是波普、欧普、朋克与嬉皮士产生的年代,文一中提及)。第二次发生在80-90年代。第一次革命以“数量”战胜“质量”,存在极大的荒蛮(请参考朋克与嬉皮文化的始末),而这种放纵和AIDS的产生也直接推动了第二次性革命,即:在这场革命中,我们要坚持一对一的关系。
虐恋行为中,有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这关系是自愿而相对稳定的,也就是从安全性考量方面,虐恋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传统行为。首先,这种关系的产生往往是建立在完全信任的伴侣之间。其次,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寻求快感,这里主要指不交换体液的行为。虐恋不等同于暴力,其基本原则是自愿而尊重,双方往往会事先约定合理可接受的范围以及被迫停止的暗号。
另一方面,受虐者多于施虐者,伴侣双方存在角色互换的情况,也就是受虐方可能是不固定的。原文中引用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一个在性关系中能够从对他人施加痛苦中感到快乐的人,也能够享受从性关系中接受痛苦的快乐。”通常意义上,虐恋双方认同的观点是“快乐至上”,也就是痛苦只是达到兴奋的路途而不是目的。
有趣的是,暴露癖行为的背后往往是某种自恋倾向,而这种倾向“有时可以在想象中完成,这种暴露或希望被人看到的冲动实际上是对性惩罚的期待。”
此起彼伏的M——被体制化的人
电影《Real》中一段对于女主宋宥华的描述(大意):一个人在童年中如果时常接触被伤害的人或动物,在长大后,容易对悲惨的人和动物产生怜悯,以致产生爱慕之情。
“虐恋已经超出了性的范畴,形成了一种受虐倾向的社会类型,它在一些个人生活和社会群体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这些现象被受苦这一阴暗的欲望所主宰,自我贬低和自我拒绝是社会受虐倾向的目标。”这里所说的“被体制化”正是指我们的社会受虐倾向。
马库斯提出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这种情形表现为“任何一个统治了一定时间的权利体系都会找到最有效的保持其身份结构的工具,也被称为错误意识。”当统治者的统治秩序被破坏时,某些受压迫者会攻击反抗者,因为这部分受压迫者害怕听到“被压迫”的本质,也就是作者形容的“‘囚徒’无论如何要同‘越狱者’保持距离。”
“马库斯认为:压迫者会尽力做到使被压迫者不会过于难以忍受。”正如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解释中,说到受虐者会对施虐者产生好感和依赖心,甚至协助他伤害自己,这情绪产生的背后往往是伴有施虐者的小恩小惠。
“弗洛伊德是最早注意到社会受虐倾向的人,他称这种倾向为‘道德受虐倾向’,心理分析的最新观点认为,它源于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从这层意义出发来解释或许可以直指我们的要害,例如宗教修行和延迟享乐都是这种受虐型的表现。太宰治在《人间失格》引用夏尔·克罗的诗句:
“日日同样的事重复不息,只需遵从与昨日无异的惯例,若能避开炽猛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哀痛来袭”
而作者在文中谈到一个德国民间故事:一个人只喜欢上山不喜欢下山,因为下山时不能不想着爬下一座山的辛苦,所以只有上山时才能产生对下山的预期和快感。两者虽不完全相同,却也有着隐隐的联系:即通过压抑自己快乐的情感来抵消对于不快乐的预期。还可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为:一个人点了苦瓜炒蛋,然而他并不喜爱苦瓜,只是出于清火的目的。于是他先把苦瓜吃尽,然后将鸡蛋作为最后的美味。虽然这三种快乐的程度是不同的(1中的快乐是相对于哀痛来说的,也就是比较而产生的快乐),却也可以解释人们从受虐中寻求快乐的特质具有相对普遍性。
所以,从这种相对轻松和广义的角度来说,标题仿佛又十分之契合。
本文内容采集自网络,侵权即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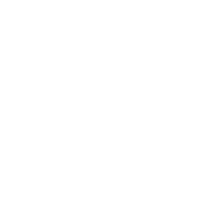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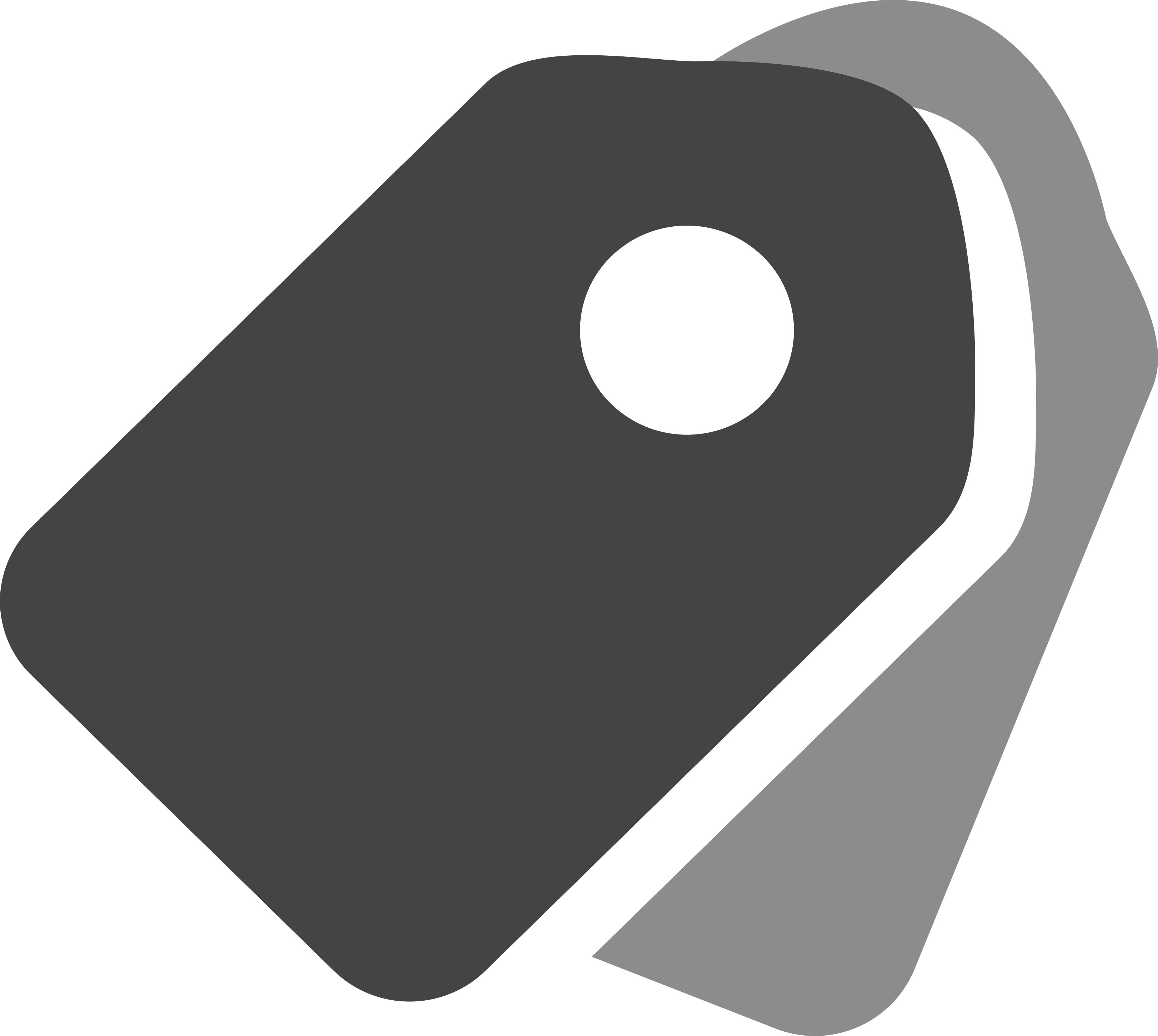
 142
142